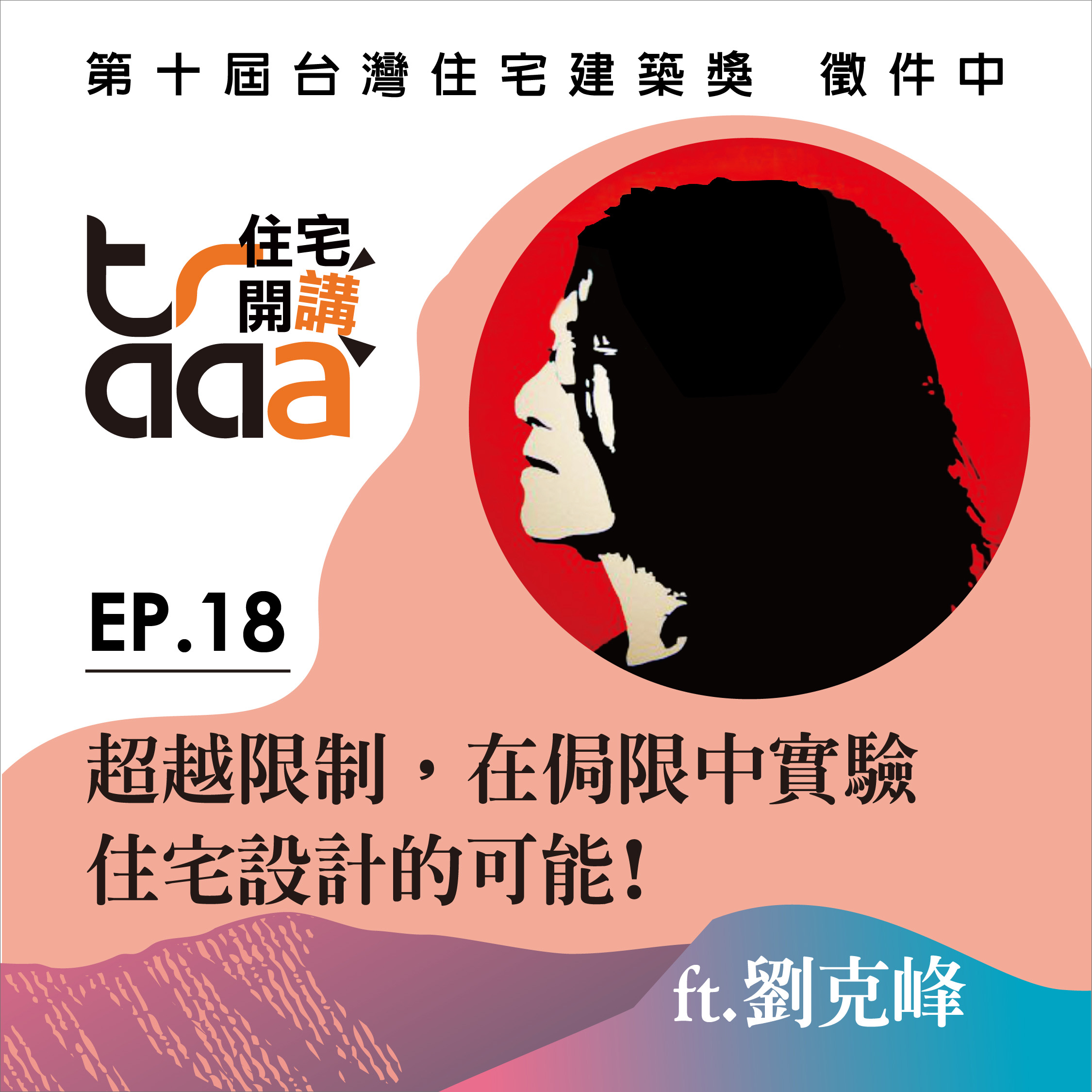- 2025 年 10 月 14 日
訪談時間:2025年7月31日
受 訪:陳亮全/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退休教授
採訪撰稿:王進坤/台灣住宅建築獎協會秘書長
王:先請亮全老師簡單介紹自己的背景。
陳:我是嘉義人,兒時住在連棟街屋中,一樓前面臨路是店面,後面跟樓上則是居住空間,念中原大學建築系後才搬至台北、住在公寓類型的住屋,後來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建築學科吉阪隆正研究室。吉阪老師的背景及其研究領域非常廣泛,不純粹談住宅建築,而是從居住環境,從人的生活、從人跟建物的關係等,多面相來談住居;所以我受其「住居學」的啟發,研究的議題不僅是建築空間,而且更從居住行為出發來思考住宅的設計,也逐漸擴展了研究領域。因此雖然是建築背景,但幾乎沒有參與建築實務,而較專注在教學研究上面。
回台灣後,任教於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初始有進行住宅研究,只是在1980年後半段當時台灣還不太重視住宅的課題,因此,開始嘗試使用參與式設計、參與式規劃的方法,在台北市雙溪福林社區進行社區環境改造,在此同時也協助文建會推動全國的社區總體營造。此外,我認為除建築環境以外,居住或生活環境的基本安全也非常需要重視,可惜當時台灣在安全防災上做得很少,直到1995年1月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後社會才開始重視此一議題,有此因緣我也轉移開始探討防災領域,且主要着重於體制建置與跨領域科技的整合,參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也擔任過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等,直到退休都在防災領域深耕。
王:台灣在防災上,面臨最大的挑戰是?
陳:防災到最後或是說其關鍵在於土地使用規劃,台灣在這部分的認知到現在仍很缺乏,政府談防災主要是救災應變,當然這方面是不能輕忽,但災害的防減才是根本;必須從上位的國土規劃就要跟防災結合,從土地使用分區等根本處來減少、避免災害發生才行,可惜國人對防災的認知仍然比較弱,導致災害頻頻發生後才進行緊急應變。
居住環境亦是如此,世界衛生組織(WHO)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居住環境的四大原則是「安全性、衛生性、便利性及舒適性」,其中第一項就是安全,但反觀台灣卻是從便利性開始談,將安全跟衛生放在後面。我認為首要應是給予居住者安全,再擴張到社區、都市,甚至國土,整個環境安全是不能忽略的,無奈政府跟民間都太輕忽,如今氣候變遷導致極端災害愈趨顯著,問題也愈嚴重,例如今年7月初的丹娜絲颱風及其後連續幾天的豪大雨就造成中南部十分嚴重的災情,因此台灣的國土、都市計畫跟建築設計的法規規範等,都必須要重新以防災、韌性的角度來加以審視、調整。
王:您為何願意接受本會邀請,擔任「台灣住宅建築學生論文獎」的評審?
陳:前往日本求學原是想做集合住宅研究的,大學也是從小住宅設計開始,只是當時根本不曉得什麼是住宅,只能靠描繪國外經典住宅建築開始,接著慢慢做到集合住宅類型的設計。畢業後在黃祖權老師事務所工作,參加南機場國宅競圖案,設計集合住宅,當時國宅坪數的標準是8坪、12坪及15坪,但卻有許多不同的家庭組成要進住、一起生活,這是很大的課題;集合住宅社區與單棟住宅非常不同,例如住戶共用的公共設施該怎麼設計?由於台灣當時對這部分沒有研究,所以決定赴日再念書。
進到吉阪研究室對我受到很大的衝擊,因他是談「住居學」,是研究居住者的居住行為,再以此為設計的基礎,這顛覆過去在台灣設計住宅的方式。且住宅是與人最息息相關的建築,佔的建築量也最高,可惜台灣過去缺乏對住宅研究的熱情,但現在或許不同了,所以這次被邀請,就想來看看近日學生們的努力成果,貢獻一點力量。
王:日本的住宅格局是怎麼演變而來?
陳:台灣建築教育就住宅而言是從空間配置教起,但日本則是從居住型態看起,非常重視居住型態的研究,日本從農業社會到現在的住宅型態改變許多,在關東大地震跟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大量供應住宅,日本政府成立了住宅營團,之後再改組成為住宅公團,提供了大量的住宅。而在這些住宅建設的歷程中,民眾的生活型態也從使用榻榻米到睡床,從通鋪到個人房間,但重要的是其改變的依據背後都有進行居住型態的調查、彙整,來做為因應居住行為改變與需求的依據,並藉此提供適當的、好的居住品質。
在他們的調查中,認為傳統通鋪的榻榻米缺乏個人隱私,也較不衛生,故開始朝向「食寢分離」,改變過去同一榻榻米上放桌子是餐廳,換床被就變成臥室的食寢合一生活型態,這些基礎研究,也成為住宅公團的住宅型態,也是台灣熟知的LDK(Living room、Dining room、Kitchen)系統,反觀台灣長期缺乏對自身住居行為的調查研究,只剩下偏重不動產角度的研究。
王:台灣三房兩廳的格局是受誰影響的?
陳:台灣早年街屋型態並非是三房兩廳格局,而可能是由二次大戰後美國顧問團帶來的新居住模式,也就是在今天仍常見的步登公寓系統中,台灣才開始有Living room、kitchen的配置,做設計時會開始隔幾房幾廳,但整體格局說法的變化也有受到日本LDK的影響。過去住宅也大多只有空殼隔間,搬進去後還要請室內設計師來因應需求敲敲打打,導致台灣室內設計非常發達,但這也很浪費資源,每次換房子,都要重新裝修。另外,台灣將房子視為不動產,是在賣空間,所以為了較多的房間數,就常硬著隔出房間,卻不考慮有無足夠的收納空間,結果導致房間放滿物品、很亂,收納是門重要的基礎研究,必須妥善設置才能讓生活跟空間井然有序。
一棟房子要能住的久,就須要有足夠空間,能依照居住人數的增加或減少來做調配,不然就只能用換屋的方式去滿足,但這方式又會涉及房價的問題。加上台灣不重視調查家庭組成及人口結構變化對住宅需求變化的影響,像現在邁入高齡社會,就會增加無障礙設計的需求,但另方面三代同堂的家戶則越來越來少等問題,這些都必須納到住宅設計中來討論,但因為沒有足夠的統計,就無法去制定政策跟擬定配套措施。
王:在您的觀察中,台灣的住宅格局是否有改變?集合住宅的公共空間該如何設計?
陳:例如過去的客廳大多受美國影響、是被重視的空間,因他們喜歡招待朋友來家裡開Party,主要是用來宴客,但現在台灣已不太會有人來家裡拜訪,故客廳的機能不斷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成為家人互相談話的場所,也可能是當作餐廳或起居室,開始轉為複合式的空間,要能同時滿足用餐、看電視、聚會、工作等需求。
而集合住宅的公共空間,則應依社區住戶的需求設置,像小家庭與高齡長輩所需要的公設就會不同。鄭人豪老師就曾分享,若社區小孩子比較多,則管理員旁的空間就很重要,因小孩下課後會先在那邊聚集、玩耍跟做功課,因有管理員在旁的空間比較安全。「公共」兩字也應該分開看,公是public、是不特定者都可使用,共則是給特定者共同使用的,集合住宅內的都應屬於共用空間,也就是給居住在裡面的人使用,必須符合住戶需要的,而且這些空間或設施會隨生活行為而改變,例如現在網路購物、外送便利,共用空間就會出現為了代收包裹、餐飲的暫存空間。所以共用空間保有可被調整的彈性,讓住戶能依自身需求的不同而調整是重要的。
建設公司開發的集合住宅公設空間,大多是從銷售角度出發,建議應該回到居住者的需求上來設置。像國外合作住宅(Cohousing)裡的住戶會互相配合,例如中庭空間會開放成為小孩子種花、養動物的地方,或退休長輩交誼的場所。有些好的集合住宅案例中,住戶還會願意奉獻所長,帶小孩子做功課、唱歌等,或舉辦同樂的比賽,雖然不是很專業但每位住戶都能參加,透過軟體經營來凝聚大家對集合住居的向心力。整體來說,台灣太重視「管理」而不是「生活」,包括「公寓大廈管理辦法」這個名稱也是如此,都著重在管理上,導致當主委非常辛苦,就像糾察隊長一樣不討住戶喜歡。
王:您曾說台灣從未認真研究「住宅」的定義,也缺乏對集合居住的思考,為何會如此?
陳:近代的集合住宅的出現是因應工業革命後,為解決大量勞工集合至一處衍生的共同居住問題。若我們認為居住是重要的課題,就必須研究什麼是集合居住,或是居住生活是甚麼,開始將台灣現有的各種居住型態進行調查、分析研究,讓大眾、建築師瞭解之後,才以此為基礎進行住宅設計。但較可惜的是現在的做法是由賣房子的人主導居住平面跟需求,建築師必須配合賣房子人的意見設計,這並不正常,但建築師也該反省,為何賣屋者比你更清楚購屋者的需求。例如像前面談到的客廳、餐廳這些空間的機能是否已有變化?為何會變化?學術機構或研究者要出來進行研究,來支撐建築師的設計等。
像2024年普立茲克獎得主山本理顯建築師提出的「介面空間」,是談「私」跟「公」中間的「閾」空間,這種公私介面空間在台灣也存在,如街屋的騎樓、部分族群原住民家屋的前庭等,都有留設這樣的空間;山本觀察到這個空間跟需求後,就將此放進集合住宅設計之中。反觀台灣的集合住宅,是從管理跟產權的角度出發,住戶間疊合或連接的介面只剩下樓梯、電梯,不然就要進到特別的共用空間像交誼廳,但在那裡人往往變得不自然,反而很難有自然形成的交誼。
這些並非都是建築師的問題,也可能是建築法規過度的限制,期許業界跟學界多些合作,由業界提供數據跟資源,學界負責研究,來打開限制,才能提升居住環境的品質。大眾也要多關心居住品質跟生活需求,不要只從不動產的角度來評估住宅。台灣很少談什麼是好的居住,除了硬體,怎麼樣的共同生活的軟體也同樣需要被重視。